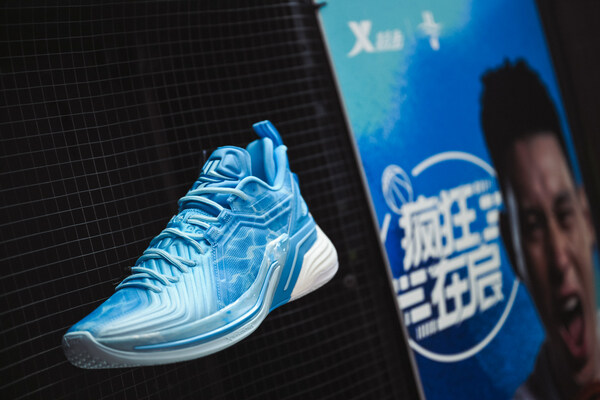“钮承泽案件”后,我们还要看多少以“恋爱”为名的强奸?
昨日(4月14日),台湾导演钮承泽性侵案件一审宣判,台北地方法院以“强制性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可上诉。
根据台北地检署公布案情,导演钮承泽在电影《跑马》拍摄期间认识了女助理A,即受害者当事人。受害者为电影剧组成员,与钮承泽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而钮承泽正是利用职务之便,对受害人实施了侵犯。
“钮承泽案”已尘埃落定,牵动人心的“鲍毓明案”却仍然悬而未决。情报君梳理了此次“钮承泽案件”的始末,发现众多“名人性侵案件”背后,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出口:即以“恋爱”为名的强奸,在所有这些案件中,受害方都被剥夺了“性同意权”。
从钮承泽到鲍毓明,我们离恶很近很近。
“钮承泽性侵案件”始末,
是初犯还是惯犯?
距离性侵案件发生,已过去了一年半。
2018年11月23日,《跑马》拍摄剧组原订召开工作会议,钮承泽临时将会议取消,改邀剧组人员到家中聚会。24日凌晨,在剧组人员离开后,钮承泽对女助理A实施了性侵犯。
面对钮承泽的侵犯,被害人表示过明确拒绝与强力的反抗意图。事发之后,A向室友求助,并在室友的陪同之下前往台北市妇幼警察队报警采证。检方于A身上发现唾液等痕迹,检测与钮承泽DNA相符,而A身上亦有多处淤青伤痕,与A描述被伤害过程一致。钮承泽被实名指控涉嫌性侵。
事发之后,法院对钮承泽进行了两次传唤,而他本人却在公布媒体前消失了两周有余。直到12月7日,钮承泽才在小学同学、律师胡原龙的陪同下,前往台北大安分局接受问询。初次露面后,钮承泽本人对媒体鞠躬以及其“钮承泽已经死了”的言论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被不少媒体指责为“虚伪”。
12月10日,钮承泽再度前往台北地检署应讯。根据台北地检署,钮承泽对此次犯案表示否认,辩称自己想与A往恋人方向发展,是双方认知出现了偏差,而对于案件细节,他都以自己当时喝醉了,不记得经过为理由作为答复。
事实是否是这样呢?案发后,台北地检署曾传唤该剧组女主管与A闺蜜作证供。女主管表示,案发当天原本是带A去讨论《跑马》事宜,而席间她感觉气氛暧昧,遂先行一步;而A闺蜜则表示钮承泽与A是上下级关系,A平时不习惯逾矩。经过调查双方LINE聊天记录,检方认定两人私下并没有互动和暧昧,也没有任何所谓往恋人方向发展的证据。
事后,钮承泽以150万新台币(约33万人民币)获得保释,但被限制出镜、出海。期间钮承泽的委任律师胡原龙辞职,引发外界猜测,一说是因为胡原龙本人也陷入官司之中,无暇打理钮承泽事宜;另一说则是胡原龙得知钮承泽并非初犯,不愿再继续代理此事。
2019年2月,由于钮承泽犯罪嫌疑重大,且本人始终否认犯罪,检察官认为其避重就轻,企图以“认知不同”卸责。钮承泽以“强制性交罪”被正式起诉,按照台湾的刑法,“强制性交罪”罪成可被判处三到十年有期徒刑。
2019年9月,网传钮承泽向受害人A付“七位数”调解金,望达成私下和解。此前,曾有传闻剧组女主管想居中协调,让钮承泽以60万新台币与A和解,但遭到A拒绝,A表示决定提告纯粹希望日后不再有人被害,与赔偿无关。
2020年4月,在钮承泽本人继续否认性侵、并想以被害人收到补偿为由申请缓刑的情况下,台北地院一审宣判,依“强制性交罪”判处钮承泽有期徒刑四年,可上诉。
案件发生之后,民间舆论集体声讨钮承泽。据台媒报道,有圈内人士匿名透露,钮承泽实际上已经是“惯犯”,在剧组曾对女性多次骚扰。
此外,台湾女性柯奂如也通过Facebook发声,支援受害人A。她透露在2007年拍摄《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时,导演钮承泽事先未与她就片中那段“床戏”进行具体沟通,而在拍摄当天她却得知该段床戏尺度极大。在拍摄过程中,钮承泽作为男主演对她的触碰令她感到非常不适。柯奂如坦言这件事让她深陷阴影,尤其是在看到成片之后,深深怀疑当时是否有必要付出那么多去拍那样一段戏。
图片来源:演员柯奂如Facebook
时至今日,钮承泽本人也没有在法庭上亲口承认犯罪事实,对于他对A造成的身体与精神上的伤害始终避而不谈。或许在他看来,这次娱乐圈狩猎行动的失手,造成的只是他名誉上的损失,而殊不知他已经被公众审判钉在了道德耻辱柱上。
迫于被“封杀”,
台湾演艺圈集体噤声
值得注意的是,性侵案件发生后,台湾的娱乐圈言论与民间舆论走向了不同的两端。
在社交网络上,绝大部分网友都非常愤慨,鉴于钮承泽在社交平台的“写诗”行为,网友认为不知悔改还大义凛然;
也有一部分网友转而将矛头指向女方,认为她骗取调解费,套路钮承泽,是所谓“仙人跳”。
这种当事人权利地位不对等的性侵案件被诠释为受害人“仙人跳”的思维并不少见。在他们看来,性侵事件发生之后,受害方是不能索要赔偿费的,如果对方支付了一大笔赔偿费,那么就一定是你狮子大开口,如果接受了这笔赔偿费还继续控告,那么就是你得了便宜还卖乖。这种第一时间把自己代入了加害者身份,并将炮火转移向受害人的言论,我们可以在不少性侵事件中发现,发言者对受害人的痛苦置若罔闻,转而为加害者开脱洗罪,殊不知自己也沦为案件的共谋。
而另一边,台湾娱乐圈几乎是集体噤声,不仅《跑马》剧组、制片方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钮承泽的圈内好友、合作伙伴谈及此事也避而远之。根据”新浪娱乐”的报道,有业内人士透露,剧组工作人员大多因为钮承泽在娱乐圈地位高、人脉广阔,而不敢对此发声,怕自己日后遭到“封杀”,也有相关人士表示:“其实就是影视资源被部分人士占据,多数人都依赖裙带关系加入,那又因为是共犯结构,所以大家都不说,也不挑起事端,就为了要继续有片可以拍。”
事实上,钮承泽“满族贵族后代”、“名将之后”的身世一直是台湾八卦娱乐的兴趣所在。钮承泽9岁以童星身份出道,33岁开始导演生涯,迄今执导过10部电视剧、4部电影,曾凭借《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获得金马奖费比西影评人奖,其执导的电影《艋舺》曾入围第60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彭于晏、阮经天、赵又廷、李威等著名台湾演员均参演过他的作品。
在台湾演艺圈,业内一向奉行“师徒制”,这种现象并没有制度可依,却切切实实存在于演艺圈人际关系中,比如侯孝贤与钮承泽、钮承泽与阮经天就以师徒关系相称,这种师徒制使得台湾演艺圈人与人之间的裙带关系更加紧密,也使得资本以结群的方式共生。
资深艺人尚不敢发声,何况是不知名小艺人,所有的沉默最后指向的都是“担心被业内封杀”。可以想象的是,这张由地位、权利交织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可能成为一些恶性事件的保护伞。对于受害者来说,它是一座无形的大山,伴随压倒性的沉默。
去年,一部以台湾演艺圈的潜规则事件为蓝本的台湾电影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竞赛单元,它就是由赵德胤执导、演员吴可熙编剧的电影《灼人秘密》,吴可熙将自己早年被羞辱、被迫裸露的经历写进《灼人秘密》中,引起业内哗然。《灼人秘密》被视作“MeToo”运动在台湾的一个结晶,掀开了台湾演艺圈剥削结构的一角。
更多的问题被隐藏在了社会现实之中,无论是在演艺圈,还是在其他地方,在强权结构中,没有个人尊严可言。
将“恋爱”合理化强奸,
将责任归咎受害者,
这样的案件还要有多少?
就在前几天,台湾演艺圈另一起性侵案件宣判:台湾艺人秦伟利用工作之便,性侵编剧和粉丝,被判刑8年;
而前几年,同样有台湾导演张作骥因性侵女编剧被判有期徒刑3年10个月。
查看案件发生后他们在公堂上的辩解,可以说几乎跟钮承泽如出一撤。秦伟将性侵归结为是自己的“感情偏差“,张作骥则认为与对方是“两情相悦”,均利用男女之间的好感将犯罪行为合理化。这其中的前台词即为,只要双方是男女朋友关系,性行为就构不成犯罪。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的鲍毓明案件。鲍精通法律,在采访中便将话题往两人处于恋爱关系上引导,更早前,他在给李星星(化名)的保证书中写道:“给我现在的女儿,未来的妻子”,几乎将受害人的尊严与身体自主权视作无物。在《财新》一篇特稿将之定性为“这更像是一个自小缺少关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后,原本集体批判的网络舆论开始倒戈。
更有甚者,之前的刘强东案件,案件发生后,刘强东将整个事件归结为是女方主动邀约,双方自愿发生的性行为,以此为自己开脱。
而微博上,一些截取的碎片视频和王思聪一句“价格没谈拢”将舆论导向了反面,网友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沉默的受害者。时至今日,距离案件发生已一年半有余,但诸如“境外势力加害”、“女方仙人跳”的言论在互联网上仍然大量存在。
可以想象,一则案件因为随便放出的几句言论、几个视频就可以出现反转,公众对于强奸案的认知该是有多么苍白,对他人的痛苦是多么冷漠。
纵观这些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一只有两股阴影萦绕不去,这两股阴影不仅对受害人造成了二次伤害,也扭曲了公众的视角。
第一股,即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女性被视作男性的附庸与私人财产,可以随意追逐、侵犯、抹黑。在性侵案件发生时,这股势力表现为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蔑视,对女性压迫和污名的信手拈来,以及对“完美受害者”的猜测臆想。
第二股,即由权利不对等催生的共谋网络。加害者是名人,享有权利、地位、资源,以及镁光灯的关注,从而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而受害者往往与加害者在地位、声望上差距悬殊,得不到更多的关注,进而被随意“涂抹”。这张网能导致的最严重的结果是,事件不了了之,加害者继续逍遥法外,受害者痛苦一生。
这两股阴影共同合力,最终的结果为,一个个本就受伤的个体被无情碾碎、践踏。
如今,钮承泽案件宣判,我们自然希望它能为当下的鲍毓明案提供样本——希望犯人被绳之以法,希望受害人能够被妥善对待,希望公正的司法永远不会迟到和缺席。
同时,我们也更希望,这些事件的相似之处能够唤醒公众对于强奸案的反思,女助理不是个例、李星星不是个例、jingyao不是个例,这样的案件每时每刻,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遍又一遍上演。
最后,情报君也在此援引已故作家林奕含的一句话:成为一个对他人痛苦,有更多的想象力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