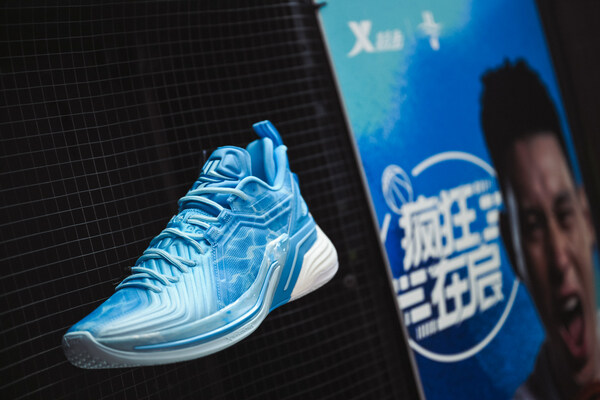隐秘角落里,行走在人间的恶童
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中说:“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能够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邪恶,并且融会贯通,使儿童不受创伤。”
但请务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基督式的“天使儿童”已经基本从媒体上消失了。走上荧幕的,是撒旦式的“恶魔儿童”。
无论是华语影视《隐秘的角落》的朱朝阳、《唐人街探案1》的思诺,还是好莱坞电影《安全邻域》《辣手保姆》里“杀人如麻”的儿童,他们都被“成人化”了。
这些影视作品,塑造了共同的儿童形象:那就是在走向恶的深渊时,他们绝不比成年人速度慢,甚至还有天真无邪的外表和《未成人年保护法》作为庇护。那份让人毛骨悚然的狡黠和乖戾,正是戏剧张力的来源。
更加耐人寻味的图景是,大人们看着“恶童”,一面细思极恐,一面津津有味。天真无邪与阴暗妒恶,这种反差让恶童们看起来“迷人又危险”。大人们都曾经是“儿童”,可当他们长大之后,却遗忘了很多儿童的“思想角落”。
《隐秘的角落》的原著《坏小孩》里,朱朝阳对两个小伙伴说:“在成年人眼里,小孩子永远是简单的,即便小孩会撒谎,那谎言也是能马上戳穿的。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小孩子的诡计多端,哪怕他们自己也曾经当过小孩。”
它用12集回答了知乎上的问题:小孩子的恶能有多恶?以及一个附加彩蛋:不会我家小孩也是同款吧?没准不少人看完剧再看自家小孩,表情都不自然了。
其实大可不必。不妨先确定一下:他有没有常年考年级第一,有没有破碎的家庭背景,有没有写假日记?
两个笛卡尔
《隐秘的角落》讲述了张东升(秦昊饰)精心策划的谋杀,被远处玩耍的小孩朱朝阳、严良、普普用相机意外纪录下来,三人用录像威胁张东升,逐渐卷入矛盾旋涡的故事。由于盒饭征兆太明显,现在硬糖君听到“爬山”和《小白船》就相当PTSD。
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从你推下第一块,便无法逆转随之而来的崩塌。本该轻松愉快的暑假,被儿童的恶意层层包裹,成为一场飞蛾扑火的计谋盛宴。
朱朝阳,是残忍角斗后的存活者,也是被现实无情吞噬的牺牲者。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即使被同学在水杯里放橡皮筋、被刻意排挤,也只是委曲求全。他的品学兼优,只是为了获得重组家庭后父亲的一丝垂怜。
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是小公主,锦衣玉食还不懂事。而朱朝阳的衣服领口都洗白了,才让父亲感到不好意思带他逛商场。在妹妹坠楼后,他被警察调查、被朱晶晶的母亲威胁。但他万万没想到,父亲也会假仁假义的用录音笔套他的话。
他故意说:“要是我和晶晶交换一下就好了,死的是我的话,爸爸现在就不会这么伤心了。”什么样的绝望和心碎,才让一个孩子说出替妹妹去死的话?父亲从小带他吃的甜品依旧美味,只不过碗上多了一只苍蝇,徒增恶心。
原著中,朱朝阳好学生的标签,成为他最好的伪装。他借此成功摆脱大人的猜疑,将罪名嫁祸给已死之人。父亲、朱晶晶的母亲、张东升,甚至是两个小伙伴,无一不在他的谋算之内。
日记本相当悚然,朱朝阳写的细节与现实严丝合缝,但每到涉及真相的关键之处,就与现实截然相反。他把自己塑造成被胁迫的弱者,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配合。
由于涉案题材的审查限制,《隐秘的角落》几乎是《坏小孩》带着镣铐跳舞的最优解。它隐藏了朱晶晶的坠楼细节,在片头动画和剧中《还珠格格》的台词里,暗示了诸多“故事的另一面”。
从朱朝阳给妈妈讲笛卡尔的故事开始,一直就存在两个版本的暗示。童话版的,笛卡尔和公主相爱却无法相守。暗黑版的,公主并不理睬笛卡尔,笛卡尔死于背叛。张东升上课也讲了两个版本,并且在被击毙前对朱朝阳说:“你可以相信童话。”
朝阳晦暗,旭日东升。朱朝阳和张东升其实是一类人,这从原著名字设定便可窥见。他们都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并希望有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张东升每次杀人前,会问我还有机会吗?朱朝阳则在日记里写:“好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啊。”
当心别进小鬼家
在《小鬼当家》里,麦考利·卡尔金击退了闯入家中的蠢贼。而在同样由他主演的《危险小天使》里,他射杀小狗、制造公路惨案、“误杀”寄居家庭的妹妹。
同样是当家,小鬼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危险小天使》的亨利,对表哥和表妹有着超出常情的嫉妒心。为了争夺母爱,他变成了可怕的杀人魔鬼。
儿童在好莱坞变成魔头boss,固然是出于悬疑恐怖类型的市场需要,但也离不开“儿童威胁论”的社会背景。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出现了系统性的动荡:种族运动声势浩大,性解放惊世骇俗,嬉皮士我行我素,儿童犯罪率直线上升。
1950-1979年间,美国儿童犯重罪率增加了11%。随着《坏种》《万圣节》《魔童村》等影片上映,“问题儿童”被塑造成一种社会性恐怖。1956年的初版《坏种》,“芭比娃娃”罗达用计谋除掉所有挡路者,表现出极端冷漠和自私。只因男孩书法比赛击败了她,就被罗达溺死水中。
1960年的《魔童村》更加诡异,美国小镇所有妇女在同一时间昏迷,醒来后集体怀孕。生下来的孩子都是一头白发,具有超自然的杀伤力。最后真相被揭露,魔童是缺乏人性的“外星移民”,是不容于世的“异种”。
1978年的《月光光心慌慌》,用菜刀杀死姐姐的男孩仅有6岁。最极端的当属1968年的《罗斯玛丽的婴儿》,凭不曾露面的“魔鬼圣婴”就把观众吓个够呛。
随着儿童威胁论的远去,新世纪好莱坞的恶童由反映社会问题退化到了“儿童性体验”。2005年的《水果硬糖》,女孩为了给朋友复仇,以身体为诱饵将恋童癖摄影师引入圈套,并进行了具有仪式感的阉割。
2016年的《安全邻域》里,12岁男孩爱上了来家里babysitter的保姆。为了向对方证明男人的无用,男孩叫来了保姆的前任和现任,并当着她的面将二人折磨至死。
与其说它是血腥版《小鬼当家》,倒不如说是极端的少年情事。在保姆面前毫无吸引力的男孩,只能通过屠杀成年男子泄愤。与之相对的,是2017年的《辣手保姆》,同样是暗恋自家保姆,男孩科尔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身材惹火的保姆Bee,不仅性格开朗还帮助科尔对抗校园霸凌。可当科尔发现Bee搞恶魔献祭并且杀人如麻时,他的好感瞬间瓦解。于是他和邻家女孩一起对抗保姆,恋爱对象由熟女退化成了同龄女孩。
“儿童不懂性”的刻板印象,在三部影片中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十分公开的表达,可以是极端变态的占有,也可以是朦胧疏离的好感,更可以是以牙还牙的逻辑。
类型化的恶童
《隐秘的角落》里朱朝阳靠一本日记脱罪。而在世界文坛,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才是该类型的鼻祖。
日记体的小说《恶童日记》,有着明显的儿童视角:乡村的破败、战争的荒芜、人心的黑暗,都通过兄弟俩的眼睛逐步呈现。他们互相拷打,学习忍受,练习挨饿,接受陌生人的蹂躏摆布。
此外,还有肮脏吝啬,叫两个外孙“狗养的”外婆、胆小猥琐的虚伪神父、邋遢放荡的兔唇贫女。甚至同性恋军官让兄弟俩撒尿到自己身上,男孩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在儿童平淡的口吻中,道德观念匮乏的生存世界铺展开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儿童作恶”的根源阐述为:“儿童在施恶时,不再像他们的双亲那样还忍痛抑苦,反而心情愉快。”正因为儿童们的社会化,使他们深知只有“恶”才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外壳,社会家庭因素是儿童的“催恶剂”。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留莎,在面包里插大头针的“恶行”,是对自身及家庭所处弱势地位的一种反抗;《白痴》中饱受疾病折磨的伊波利特,临死前的心愿是作弄迫害他一辈子的那些人。
而在东亚,恶童文学的集大成者当属东野圭吾。比起展露无遗的雅歌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笔下的恶童多了一层隐蔽的寒意。家庭和校园的阴暗面,往往作为惨案的背后推手。
《红手指》中的中学生直巳,成长环境畸变。当直巳母亲说儿子初露猥亵幼女的端倪时,直巳父亲并没有及时制止,酿成了儿子掐死小女孩的悲剧;《彷徨之刃》中的敦也,被逐出家门后在独居公寓绑架杀害了无辜少女。
《白夜行》的女主唐泽雪穗,被母亲卖作童妓。而喜欢雪穗的桐原亮司,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强奸雪穗。亮司用剪刀杀死了父亲,此时两人都只有11岁。他们不仅是欺骗杀戮的施害者,也是被成人世界侵袭的受害者。
中国当代文学也不乏恶童的身影,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余华《现实一种》中的皮皮、王朔《动物凶猛》中的马小军、李铁《王国》中的王宝明,都是童真土壤里开出的“恶之花”。
恶童的堕落,不能全赖在社会家庭上,它更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工具理性”。理性沦落为支配与操纵人的工具,追求利益和机械目的在某种层面不谋而合。原本荒诞无稽的行为逻辑,成为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
抑或,童年本就存在着一套隐形的权力结构和欲望机制,这套结构正是成人世界权欲的雏形与策源地。